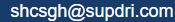《邻里东京》导读
《邻里东京》导读
【美】西奥多 C 贝斯特 著 国云丹 译
书评作者:韩小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硕士研究生;何丹,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副教授,博士
邻里社区(即“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其生存发展状态与整个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然而,我们对当代都市邻里社区的历史发展轨迹、地方政治、社区组织、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内容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似是而非的状态。为了揭开邻里社区的朦胧面纱,著名的人类学家西奥多.C.贝斯特(Theodore C. Bester)通过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及多次回访追踪,对东京当代都市邻里进行了全方位、零距离的考察和探访,最终在《邻里东京》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他珍贵的研究成果。
贝斯特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曾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现为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及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他关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著作广博而精深,尤以当代东京的民族志研究而著名。《邻里东京》于1990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都市与社区研究大奖,是当代都市人类学的代表之作。
作者在《邻里东京》这本书中,主要驳斥了3个关于城市邻里历史发展和社会特征的主导观点:(1)东京是一系列乡村的集合,(2)城市邻里仅是一个行政的或政治的术语,(3)传统城市邻里生活的稳定性是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
作者在前两章中对宫本町及其历史进行概述。通过介绍宫本町的地理位置、界限范围、空间布局、人口、交通和地标性建筑等基本信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时空兼备的日常生活画卷。作者认为邻里呈现出的稳定的生活模式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潮流,是“传统主义” 的结果,而非独立于社会变迁过程的老中产阶级继承乡村或是前工业时代“传统” 的表现。通过梳理宫本町及其所在地区的历史,作者认为宫本町地区在经历了关东大地震和二战这两次激烈冲击之后,人口结构、经济生活和政治组织都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切断了与19世纪乡村、战前邻里的任何联系。都市邻里的建立是本地居民在人口增长、都市扩张和经济变迁过程中对安定平稳环境的渴望,以及政府对社会秩序威胁的回应,是在城市环境下产生发展而成的社区。
作者在第三章、第四章中考察了宫本町地方政治和行政,及社区服务和邻里活动情况。作者指出,通常将邻里组织视为制度的和行政的单一维度进行研究的前提是假设组织结构的正式特征创造了其非正式的一面,从而忽略了对社会的和非正式特征的多维度的研究。但实际上,宫本町的地方政府并未能完全领导邻里组织、主导邻里生活。町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似亲密而稳定,实则存在着紧张和潜在的冲突。政治和行政作用的确使宫本町成为一个可识别的单位,并为其划定地理的和社会的边界。然而,当邻里为了进一步实现它的政治目的或满足政府需求而推行一些计划和活动时,它也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从而加强居民间联系,促进邻里认同感——町会和其他地方组织是宫本町居民自我创立、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由此可见,政治的或行政的目的只是邻里的基本特征,而地方组织通过提供社会服务、组织邻里活动以增强邻里的团结和居民认同感对使宫本町成为一个独立个体来说更为重要。
作者在最后三章对宫本町内部正式的权力层级结构和非正式关系体现的平等精神进行介绍,并指出二者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家庭组—代表、地块—联络人员、片区—副主任、町会—町会干部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单位及相应负责人的形式组成了宫本町的社会等级。在决策、策划和执行邻里活动中,町会的社会等级特征会凸显出来。但是在邻居和朋友等非正式交往中,个人关系往往缺乏等级结构,体现出平等主义精神。最终,老中产阶级设定自己的标准将“新中产阶级”排除在地方权力体系之外,而他们则成为骨干成员,屏蔽了日本社会以教育和职业状况为基础来确认地位和声望的标准,建立起“地方化的地位等级制”,但他们又通过地方组织和各种公共活动强调社区团结和平等主义。
作者在结论部分着重对老中产阶级进行分析探讨并认为:(1)老中产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在维持和创造城市邻里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2)他们并非独立于社会变迁潮流之外,而是以“传统主义”形式创造“即时文化” 以回应社会环境。
就目前来看,贝斯特对于都市社区研究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宫本町详尽的民族志,使我们了解了东京的一个邻里独特的运作方式。政府机构和居民自治组织的行为关系和行为边界一直是社区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央政府长期的集权政体与地方市民化的长期博弈,在町层面形成了较为明晰的行为边界和复杂微妙(冲突与稳定并存)的行为关系。不可否认的是政府机构对社区治理和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而市民自治组织则在改善社区服务和邻里居民经济和社会状况、倡导平等精神以加强团结和社区认同感、聚集政府和社会资源等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在中国,地方组织基本上为“政府主导型”,市民社区尚处于构建状态。而“推土机”式的拆迁和门禁社区“泛滥”的城市更新运动在重塑城市形象的同时也摧毁了原有的社区传承和地方认同。另外,快速城镇化浪潮下形成的“都市乡村”和近郊乡村邻里也因“城市移民(或农民工)”的入驻而改变了甚至是割裂了邻里的组织结构、行为方式和地方认同的历史传承,往往形成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行为主体的权益博弈、管理缺位和认同缺失的复杂局面。类比于东京,或许社区认同重构和行为规则重建正是扭转政府主导社区的情势,增强地方自治意识和能力的契机。中国城市社区如何重构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零距离”探究。